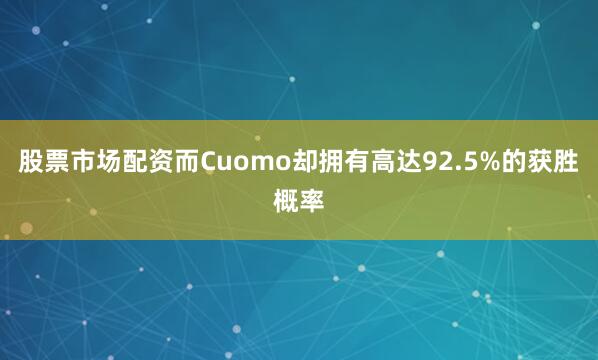在广袤的鹑觚原上,麦浪翻涌成海,青纱帐摇曳成歌,高粱穗垂着红玛瑙,荞麦花染紫了山梁。这里的人们让平凡的粮食绽放出最温暖的人间烟火——那枚直径尺五、厚约八分的锅盔,便是长武人写进岁月里的“文化密码”。
从战场到民间的“生命之饼”
长武的锅盔,名字里就带着刀光剑影的印记。俯瞰这片土地,县城以北的浅水原,是李世民大破西秦霸王薛举父子的古战场;县城以东的黑水古渡与阴灵关,是唐代“靖难军”扼守西北的险隘;县城以西的古长武城,更是唐代“神策军”八镇之一的军事要冲。两千多场战事在这里上演,而锅盔,正是将士们征战时的救命干粮。
它耐储藏、耐携带,烙得金黄酥脆的面饼能存半月不霉;它口感扎实、麦香浓郁,咬一口便知是能扛饿的主食;更奇特的是,紧急时刻,这圆滚滚的锅盔还能当“盾牌”。史书记载,唐军守阴灵关时,士兵们用锅盔挡过冷箭,用麦香鼓舞过士气。久而久之,制作锅盔的手艺在长武生根,从军帐里的应急粮,变成了农家灶台上的日常主食,又从日常主食,演变成了承载礼仪与情感的文化符号。
展开剩余72%揉进麦香的岁月温度
王大妈女儿快临产了,她天不亮就起了床,案板上的面粉堆成小山,酵面、碱水、北水沟的山泉水早已备好。“面要揉足三百下,锅盔才筋道。”她一边念叨,一边把面团摔在案板上,“咚咚”的声响里,是四十年揉面的功底。
最见功夫的是压面。王大爷把揉好的面团搭在固定在墙上的长压杆下,右腿盘住压杆末端,右手压、左腿推,面团在杆下“吱呀”作响,渐渐从蓬松变得紧实。
面压好了,王大妈擀成圆饼,放进平底浅锅。麦草火“噼啪”窜起,锅边腾起白雾,面饼慢慢泛起金黄。“得翻三次面,每面烙三分钟。”她盯着锅,像守着贵重的宝贝。掀开锅盖的刹那,麦香裹着热气涌出来,清冽中带着点甜,仿佛黄土高原的风里,突然飘来了江南的稻花香——那是土地与双手共同酿成的味道。
一枚锅盔里的牵挂与祝福
锅盔的香,不仅在嘴里,更在长武人的习俗里。王大妈把烙好的锅盔扣在亲家的锅盖上,“咔”地一拳击破——这是“打锅”,寓意“破灾祈福”,希望女儿顺顺利利生下孩子。随后,她站在窗外把裹肚抛进女儿房间,又把裹肚压在土炕的席子底下——这是“安家”,愿小外孙落地生根,平安长大。
小外孙出生的第三天,“下奶”的礼篮里,锅盔仍是主角。王大妈带着鸡蛋、红糖、挂面,还有新烙的锅盔,敲开女儿的家门。“趁热吃,这锅盔配羊肉汤最香。”她把锅盔掰成小块,泡进滚热的羊汤里,汤汁浸透饼心,咬一口,麦香、肉香、奶香在齿间炸开,连汤都鲜得人直咂嘴。
两家人围坐在一起,看新生儿可爱的小脸,听王大妈讲“当年我生你时,你姥姥也是这么‘打锅’的”,笑声撞着锅盔的香气,在屋里暖成一片。
从乡土到中国的“长武味道”
如今的长武锅盔,早已不是农家灶台上的家常饼。它直径尺五、厚约八分,比武功西府锅盔更筋道,比乾州锅盔更纯粹,带着北水沟山泉水的清冽,带着麦草火的烟火气,更带着长武人实在的性格——不花哨、不矫饰,把最本真的味道捧到你面前。
它是游子行囊里的乡愁:在外打工的小张,行李箱里总塞着两个锅盔,“闻着这味儿,就想起妈烙饼时的样子”;它是外地游客的惊喜:今年的马拉松比赛现场,1000多鏊锅盔瞬间销售一空。它更是长武递给中国的“文化名片”,当外地的客商、学者踏上这片土地,一碗羊肉泡锅盔,便让所有的陌生都成为回家的亲切。
从古到今,长武锅盔用千年的时光,把历史揉进面里,把温情烙进饼中。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长武人“以食为媒”的生活哲学——用最质朴的方式,把对土地的敬畏、对家人的牵挂、对传统的坚守,都酿成了舌尖上的烟火,酿成了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
这鏊锅盔,是鹑觚原上的月光,是麦浪里的风声,是长武人写给全中国最温暖的情书:来长武了,就尝尝我们的锅盔,那是家的味道,是历史的味道,是长武的味道。
作者:白曙红
发布于:北京市冠达配资-股票配资开户费用-网上炒股配资-专业炒股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